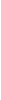64道理
南淮身着紫袍,本就有几分姿色的脸,因为受到惊吓多了几分楚楚可怜。
他扶着随侍的手,因为不敢得罪大隆权贵,只能面色惶惶地站在路边。
看到马车里出来的人是云拂衣后,他明显放松了许多,松开扶着随侍的手,上前作揖行礼:“小王见过云郡主。"
“王孙不必多礼。”拂衣回了半礼,她的马车没有什么大碍,南淮的马车已经歪歪斜斜,明显不能再乘坐:“真巧。”
大理寺门外的主动问路,彩音坊的巧遇,今日的马车相撞。若没有这些巧合,她一个朝臣之女,与南淮这个南胥国质子不可能有什么交集。
“王孙,您还要赶去崇文馆念书,现在马车坏了怎么办?”随侍看着撞坏的马车,焦急道:“要不奴才替您给先生告假?"
“不行,先生最不喜懒惰的学生,更何况能在大隆学习是我们南胥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,我怎么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?”南淮对拂衣歉然一笑:“云郡主,家仆无知,请您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”
“嗯。”拂衣点头:“放心,我不会去告状。”崇文馆的那些老头子看到她都吹胡子瞪眼睛,她才不会傻到去送骂。
“郡主,在下有个不情之请。”南淮拽着身侧的袍角,既胆怯又可怜:“能不能……麻烦您送在下一程?"
说完,他似乎觉得自己提的请求有些冒昧,白嫩的脸与脖子顿时泛红,低着头不敢看拂衣。
“既然是不情之请,王孙就不该开口。”岁庭衡掀开帘子,居高临下地冷眼打量这个搔首弄姿的南胥王孙:“王孙—心向学,又怎能惧这条求学之路?”
“拜见太子殿下。”南淮神情惊惶地向岁庭衡行礼,下意识向拂衣投去求助的眼神。
“太子殿下说的是,是在下僭越。”南淮皱着眉:“只是在下的脚受了伤,若是一路走到崇文馆,只怕走到午时都赶不上。"
岁庭衡见他这副模样,在心中冷笑,都是男人,谁看不出他那点小心思。
他走到拂衣身边站定,毫不掩饰他与拂衣之间的亲密:“南胥王孙,往你身后左方看看。”
南淮闻言转身看去,几辆驴车停在旁边,驴车的主人正在路边邀客,一头驴子发出粗噶难听的叫声,蚊虫在它周身飞来飞去,即使看一眼都能想到它身上有多脏多臭。
南淮抿着嘴没有说话,只是小心翼翼看了太子一眼,又偷偷看了拂衣一眼。
“殿下眼神真好。”拂衣似乎没有注意到南淮的眼神,笑着对南淮解释道:“王孙不用担心,这些驴车都在京兆府登记造册过,价格合理公道,童叟无欺,你放心乘坐,绝对不会语骗你的银钱。"
“至于我的马车……”她回头看了眼自己的马车,叹口气道:“看在你远赴异国他乡的份上,就不用你赔偿了。“
“郡主心善。”理王府的太监瞥了眼南淮:“按照我们大隆的律法,马车不按道行驶,造成他人损伤,以下犯上者不仅要赔偿车主损失,还要受杖责之刑。"
“王孙刚来大隆不久,不知道我朝律法也是情有可原。”岁庭衡牵住拂衣的手:“既然云郡主不愿意追究,王孙就退下吧。"
“是。”南淮低头行礼:“多谢太子殿下与郡主对在下的宽恕。”
岁庭衡看着他低着的头,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,牵着拂衣回到了马车上。就这点手段也想勾引他家拂衣,真是可笑。
“王孙,太子与云郡主离开了。”等马车一走,随侍立刻小声提醒:“我们现在怎么办?”
南淮抬头望着远去的马车,脸上的笑容与讨好没有半点变化,眼瞳黑压压沉了下来。
都说云拂衣虽行事嚣张,但有怜贫惜弱之心,上能与帝王共膳,下能与码头脚夫同行,京中好友无数。
他第一次向云拂衣问路时,她对他的态度确实没有上国勋贵的高傲。
她也并不惧怕离岩国,可是离岩国使臣在彩音坊羞辱他时,不仅她冷眼旁观,就连她的那些所谓的友人们,也无一人前来相助。
今天他精心打扮一番,本以为有机会靠近云拂衣,不曾想马车里还坐着一个太子。
身为太子,不坐自己的太子车驾彰显身份,反而挤在区区郡主车驾之中,隆朝太子难道不在乎自己尊贵的身份?
“去坐驴车。”南淮转身朝驴车走去。“可是王孙…….”随侍抓着书袋跟在他身后。
“隆朝太子好意指点,我既一心求学,就不能拒绝这份好意。”南淮眼神越发阴冷:“上国太子的话,你我谁能违背?“
“可是若被其他几个国家的使者知道,他们会嘲笑您的。”
“都是质子,他们又有何资格瞧不起我。”南淮停下脚步,看着这个繁华的京城:“终有一日……"
就算再厉害的雄狮,也有老去倒下的一天。即使再小的蚊蚁,也能在倒下的雄狮身上咬下血肉。
“拂衣觉得南淮容貌如何?”踏进理王府大门,岁庭衡突然开口。
拂衣惦记着理王府厨娘给她做的酥山,听到岁庭衡乍然这么一问,想也不想便道:“南淮是谁?”
“南胥国的那位王孙。”
岁庭衡拉着拂衣在内殿坐下,屋内摆着冰盆,拂衣舒适地往椅子上一仰:“我没怎么注意看,下次我认真看过后,再回答殿下这个问题?"
岁庭衡打开折扇走到她身边坐下,似笑非笑地替她摇着扇子:“当真没认真看?”
感受到凉风,拂衣把脑袋朝岁庭衡方向挪了挪:“嗯嗯。”
见她主动亲近自己,岁庭衡笑了:“既然你未认真看他,说明他没有过人之处,下次也别看了。"
“殿下。”拂衣仰头看他:“难道你在吃醋?”
少女上扬的唇角,带着笑意的眼睛,都让岁庭衡忍不住心动。他伸手为她理好鬓角处凌乱的发丝,情不自禁俯身用唇角轻触她的额头,低声道:“你说得对,我吃醋了。”
近在咫尺的俊美脸颊上露出委屈了表情,拂衣心头酥酥麻麻,捧住他的脸在他脸颊边吧唧一口:“殿下仙人之姿,有你在我身边,我哪里还看得见其他儿郎?”
被拂衣主动亲了一下,岁庭衡先是恍惚,随后眼中迸出灿烂的星光,他看着拂衣,浑身上下的快乐几乎要凝结成形,化作快乐的麻雀,在整座京城里欢唱。
莫闻端着冒着寒气的酥山站在门外,瞧着太子殿下一边帮云郡主打扇子,一边笑得不值钱的模样,赶紧低下头:“殿下,膳房送来了酥山。”
“快呈上来。”拂衣抬头看向门外,发现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宫女太监。理王府的酥山,比民间卖的酥山讲究精致许多,就连碗都是晶莹剔透的琉璃盏。"味道如何?"岁庭衡等拂衣吃下第一口酥山,开口问了起来。
“殿下,张嘴。”
说完,拂衣把一勺酥山喂进他嘴里:“好吃吗?”这是……拂衣用过的勺子。
岁庭衡连口里的酥山是什么味儿都感觉不到,只知道晕乎乎点头。莫闻看着托盘里无人端起的那碗酥山,恨不得自己变成墙角的落地大花瓶。
“我知你夏日喜用凉食,只是外面鱼龙混杂,我担心你被人暗算,所以前些日子在王府安排了会做民间小食的厨娘。”岁庭衡不想拂衣误会他想控制她,补充道:“你若是喜欢,等从行宫回来,我就把她们送到云府。"
“原来是殿下特意为我准备的。”拂衣这才明白,为何没有主人居住的理王府,还会有做小食的厨娘。
是上次酥山里有毒的事情,吓着他了吗?
“多谢殿下,等我们从行宫回来,我就把厨娘带走啦。”
“好。”岁庭衡看着拂衣手中的勺子,希望拂衣再喂自己一勺。他精心的安排,没有被拂衣嫌弃。
看懂了岁庭衡的眼神,拂衣又舀了一勺喂到他嘴边。她家殿下这么好,她哄哄他又怎么了?
“哈!”即将抵达行宫时,林小五终于反应过来,太子殿下这是借着她的名义,向拂衣示好呢!男女同行赠行友人,大多是什么关系?夫妻或是兄妹。
城门口那么多人看到太子与拂衣送她,谁见了不说太子与拂衣感情好?真没想到,往日里瞧着完美无缺的太子殿下,也会用这种手段。林小五皱着眉在马车里换了几个坐姿,脸色渐渐好转过来。太子身份贵重,他肯为拂衣花心思,说明他对拂衣确实真心一片啊。
他明明可以用权势压人,却从有过这种举动,反而处处体贴,甚至待她们这些拂衣的朋友,都比往日温和。
这样一想,也挺好。
“八百里加急,前方避让!”"八百里加急!"
林小五一行赶紧把官道让了出来,她掀起帘子看着奔向行宫方向的骏马,皱起了眉头。发生了什么事?
“离岩国使臣团在离岩与我朝交界处遇刺,六皇子断了一条手臂?”皇帝看完这封八百里加急的信件:“既然是两国交界处,跟我们隆国有什么关系,说不定是他们自家人内斗暗箭伤人。”
“陛下,离岩国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”杜太师忧心忡忡道:“若是起了战事……
“若是离岩国敢如此不讲理,那便留太子监国,朕去前线御驾亲征。”皇帝把信放到桌上,神情凛冽:“朕为天子,自当为天下百姓守国门,护天下山河。”
众臣欲劝,可是面对帝王如此坚毅的表情,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“陛下。”最后还是杜太师开了口:“离岩国态度不明,我们暂且等等。”
“陛下放心,户部一定会作好战前准备。”云望归道:“若离岩国讲理自然是好事,若他们仍如往常狂妄无礼,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"
众人扭头看云望归,不是,你怎么都不劝劝的?
太子与拂衣听闻此事后,也都赶回了行宫。他们刚回到行宫,就传回了离岩国的最新消息。
离岩国传来国书,大意是相信此事与大隆无关,定是周边宵小挑拨离间,所以他们要对周边小国一个教训,希望大隆不要误解他们。
“陛下态度强硬以后,离岩国反而变得讲理起来。”拂衣越发觉得先帝软弱无能得可笑。
“离岩狼子野心,我们还是要加强戒备,不能放松警惕。”皇帝有些失望,把国书塞到岁庭衡手里:“朕还是比较欣赏离岩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”
离岩国行事张狂多年,听闻自家王子断了条胳膊,气不气?气啊。
可是隆朝的现任国君明显与前任皇帝不一样,动不动就想御驾亲征,他们离岩连续两年粮食欠收,拿什么跟隆朝打?
可若是不做出点反应,其他国家怎么看他们,天下百姓怎么看他们?!
离岩国皇帝想了半夜,连夜找来堪舆图,在上面指指点点,那就在周边挑个不顺眼的国家打吧。打不了隆朝,还打不了你吗?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,南胥?